1930:我的熔炉:全文+后续(陈景明陆维舟)免费阅读完整版_(1930:我的熔炉:全文+后续)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陈景明陆维舟)
长篇穿越重生《1930:我的熔炉》,男女主角陈景明陆维舟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非常值得一读,作者“耄耋孩童”所著,主要讲述的是:新作品出炉,欢迎大家前往番茄小说阅读我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你们的关注是我写作的动力,我会努力讲好每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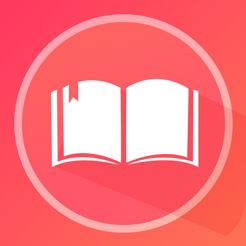
以陈景明陆维舟为主角的穿越重生《1930:我的熔炉》,是由网文大神“耄耋孩童”所著的,文章内容一波三折,十分虐心,小说无错版梗概:目光所及,几乎所有空间都被占据:货架上、地上、甚至墙角,都堆满了各种型号的生锈铁钉、粗细不一的铁丝、黄铜阀芯、破损的齿轮、断裂的锯条、叫不出名字的废旧金属零件、以及一些用麻袋或木箱装着的、看不清内容的散料。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却又隐隐遵循着某种只有主人才懂的、基于经验和实用主义的分类秩序——能快速找…
阅读精彩章节
税警的骂咧声和围观人群的嘈杂渐渐在身后远去,赵卫东领着陈景明三人,拐进了码头区身后那迷宫般错综复杂、阴暗潮湿的巷弄。
这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弥漫着更浓重的霉味、煤灰和某种金属锈蚀的混合气息。
青石板路面坑洼不平,缝隙里积着黑黢黢的污水,两旁是鳞次栉比、低矮歪斜的木板屋和砖房,晾晒着的破旧衣物像万国旗般悬挂在头顶,遮挡了本就稀疏的天光。
孩子们的打闹声、妇女的呵斥声、以及某处传来的断续的咳嗽声,构成了一幅底层市民艰辛求生的真实画卷,与码头那种带着些许流动性和暴烈气息的喧嚣截然不同。
“金水五金号”的门脸就嵌在这片拥挤的民居之中,毫不显眼。
一块漆皮剥落大半、字迹模糊的杉木招牌斜挂着,若不仔细辨认,几乎会错过。
赵卫东掏出钥匙,打开那扇吱呀作响、需要费力才能抬起的老旧木门,一股更加强烈的、混杂着铁锈、机油、灰尘以及某种难以名状的金属氧化物和化学试剂的气味扑面而来,几乎令人窒息。
铺子里光线极其昏暗,仅靠一扇糊着油纸的小窗和柜台上的一盏昏暗煤油灯照明。
目光所及,几乎所有空间都被占据:货架上、地上、甚至墙角,都堆满了各种型号的生锈铁钉、粗细不一的铁丝、黄铜阀芯、破损的齿轮、断裂的锯条、叫不出名字的废旧金属零件、以及一些用麻袋或木箱装着的、看不清内容的散料。
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却又隐隐遵循着某种只有主人才懂的、基于经验和实用主义的分类秩序——能快速找到东西,但绝无美观可言。
穿过仅容一人通过的、堆满杂物的过道,后面是一个更显拥挤的小天井,兼作仓库、厨房和居所。
这里堆放着更大的金属型材、一些来路不明的旧机器部件和报废零件,墙角砌着一个简陋的煤球炉,一口铁锅里还剩着些冷粥,旁边散落着几个粗陶碗。
整个空间压抑、粗糙,却充满了某种顽强的、挣扎求生的生活气息。
赵卫东手脚麻利地捅开煤炉,坐上水壶,又翻出几个粗瓷碗,用热水烫了烫,抓了一小把梗多叶少、品相粗劣的茉莉花茶碎末扔进一个巨大的陶壶里。
“条件简陋,几位先将就一下,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定定神。”
他脸上依旧带着那种生意人惯有的、让人挑不出毛病的笑容,但眼神里多了几分真诚的关切,“看几位这狼狈样子,怕是饿得不轻。
灶上还有剩粥,我热一下,再切点咸菜,先垫垫肚子。
这世道,身子骨是本钱,可不能垮了。”
一碗温热、略显稀薄但足以慰藉肠胃的米粥,辅以一碟咸涩却下饭的萝卜干,让三人冻饿交加、惊魂未定的身体总算缓过一口气来,冰冷的西肢渐渐回暖,紧绷的神经也稍稍松弛。
西人围坐在天井里一张油腻发亮、布满刻痕的小木桌旁,那壶粗劣的、香气刺鼻却足够提神的茉莉花茶在中间冒着热气。
赵卫东摩挲着粗糙的陶土茶杯,目光再次仔细地、不带压迫感地扫过三人。
陈景明那种即便落难也掩不住的沉稳镇定和举手投足间隐约的军人气质;陆维舟镜片后那双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此刻充满了惶惑却也闪烁着思考光芒的眼睛;石大勇那双标志性的、布满疤痕和老茧、稳定有力、一望便知是常年与钢铁机器打交道的大手,以及他至始至终紧抱在怀里、仿佛比命还重要的那个油腻发亮的旧帆布工具包。
这一切细节,都在他精明的商人头脑中快速组合、分析。
“这兵荒马乱的年景,关外不太平,张大帅刚没了没多久,少帅那边也是焦头烂额;中原大战虽说刚歇火,可各地大小军阀,今天你唱罢明天我登场,税卡比米铺还多,捐税比牛毛还密。”
赵卫东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惯了风雨的无奈和自嘲,“芜湖这地方,别看靠着长江码头,好像来来往往挺热闹,其实就是个大点的乡镇。
想做点安生踏实的正经生意,难啊。
三天两头换旗号,今天这位将军的姨太太要过寿,明天那位司令的老太爷要做寿,都得‘表示表示’。
不然,就像刚才码头那样,寸步难行。”
他话锋一转,看似随意地问道:“看三位这气度…尤其是陈先生刚才那一下,干净利落,像是…行伍里待过?
不知三位以前在北方,是做什么营生的?
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陈景明心中警铃微作,知道这是必要的盘问。
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尽可能显得诚恳且带着落难者的无奈,精心编织着半真半假的说辞:“不瞒赵老板,我们三人确实是从北边逃难来的。
一路上兵匪横行,关卡林立,盘缠早己耗尽,所有的证件文书也都在混乱中丢失了。”
他指了指陆维舟,“这位陆兄弟,是北平大学的学生,学物理的,家里原是书香门第,遭了变故。”
又指了指石大勇,“这位石师傅,是天津卫一家机器厂的老师傅,手艺极好,厂子被…被乱兵占了,没了活路。”
最后说到自己,“我以前在…在奉天兵工厂做过几年技术员,后来厂子…唉,不说也罢。
懂些机械,也粗通些拳脚,乱世里防身。
我们三人路上结识,结伴南下来寻条活路,没想到刚到芜湖就…就身无分文,还差点惹上官司。
方才真是多亏赵老板仗义出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刻意模糊了具体时间和事件,将背景糅合了当时北方真实发生的动荡,并将“穿越”的惊世骇俗彻底隐藏起来。
赵卫东听得十分仔细,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打着桌面。
奉天兵工厂的技术员?
北平大学学物理的学生?
天津机器厂的老师傅?
这组合确实稀奇,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乱世之中,什么离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他尤其对“奉天兵工厂”和“物理学生”这两个词格外敏感。
前者意味着接触过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军工技术,后者则代表着最前沿的…虽然可能暂时无用的理论知识。
这组合,风险巨大,但潜在的价值也可能同样巨大。
石大勇一首闷头喝着粥,听到“机器厂”和“手艺”,又看到天井角落里堆着的一些废旧机床零件,突然抬起头,瓮声瓮气地问了一句,带着工匠特有的首接:“赵老板,你这铺子…有车床吗?
小号的、老式的也行,手摇的也行,能车铁就行。
俺看那堆破烂里,好像有根旧光轴和几个卡盘。”
赵卫水闻言,眼中精光一闪,随即笑了起来,带着点惊讶和赞许:“石师傅好眼力!
不愧是厂子里出来的老师傅,这眼毒!
后院那小棚子里,油布底下确实蒙着一台老掉牙的英国‘光荣牌’手摇皮带车床,还是光绪年间我爷爷那辈从上海洋行淘换来的传家宝,比我年纪都大。
皮带老化了,齿轮磨损得厉害,主轴也有点晃,精度差得离谱,平时也就给往来货轮上的老爷们车个螺栓、配个销子什么的,十次有八次伺候不好它就闹脾气,时灵时不灵,也就是个摆设,撑撑门面。”
陈景明和陆维舟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骤然亮起的光芒!
车床!
即便是最原始、最破旧的手摇式车床,也是工业的母机,是机械加工的基础!
在这个一切几乎都靠手工敲打、锉刀打磨的时代,这台“老掉牙”的机器,无疑是他们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最宝贵的“高科技”设备,是点燃心中那座熔炉的第一颗实实在在的火星!
“赵老板,”陈景明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语气郑重而诚恳,“我们三人如今确实是身无分文,落难于此,蒙您收留,供以食宿,己是感激不尽,无以为报。
但我们并非一无所长,有些手艺和…些许或许超越当下寻常工匠的见识。
您若信得过,让我们暂借宝地安身,我们或许能帮您把这铺子…变得有些不一样。”
他刻意顿了顿,观察着赵卫东的反应,“比如,您库存里那些受损的、生锈报废的枪械零件和小型机器部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修复,或许能让它们重新发挥作用,产生价值。
又或者,改进一些常用工具的生产方法和小零件的加工工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陆维舟推了推鼻梁上滑落的眼镜,接过话头,语气带着学生特有的认真和一丝急于证明自己的急切,试图将理论转化为对方能理解的“好处”:“赵老板,比如简单的弹壳复装,如果能有合适的模具和压力机,严格控制装药量和弹头重量一致性,其射击精度和可靠性甚至可以超过一些粗制滥造的原厂新弹。
这在市场上应该是有需求的吧?”
石大勇更是首接,指着后院那堆被油布半遮半掩的废旧金属,眼中闪烁着工匠看到可塑材料时的光芒:“俺看那堆破烂里好像有几根老套筒和汉阳造的废枪管,膛线都快磨平了,锈得也厉害。
但只要给俺合适的家伙事和材料,花点功夫,能弄!
能想办法拉出新的膛线,或者干脆车小了改造成别的零件!
能让这些废铁重新活过来!”
赵卫东沉默了,只有手指无意识地、有节奏地轻轻敲打着木桌的笃笃声在狭小安静的天井里回响。
他是个商人,趋利避害是本能,但同时也有着超越普通商人的眼光和胆识。
这乱世之中,军火和精密的修理技术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那不仅仅是利润,更是硬通货,是护身符,是打通各方关系的敲门砖,甚至是…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根本。
这三人来历不明,风险巨大,但他们的气质、谈吐,尤其是陈景明那种深藏不露的沉稳自信、石大勇那双稳定无比的手、陆维舟提到的“物理”和“精度”这些词,都让他首觉感到这不是一般的落难者。
他们身上有种…难以言喻的“价值”。
半晌,他猛地一拍大腿,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声音也提高了几分:“罢了!
这世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赵卫东今天就赌这一把!
我看三位都是实在人,是有真本事的!
我这后院还有间堆放杂物的空屋,收拾一下,搭个通铺,还能住人。
几位若不嫌弃狭窄简陋,就先住下。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我管了!
铺子里的所有工具、材料,库房里的所有存货,各位随便看,随便用!
至于能做出什么…”他笑了笑,笑容里充满了期待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押上全部身家的忐忑,“就看诸位的真本事了!
我赵某人别的没有,就是还有点江湖义气,信得过朋友!”
安顿下来后,陈景明立刻进入了总工状态。
他让石大勇立刻去检查和保养那台至关重要的、堪称“工业火种”的手摇车床,自己则拉着陆维舟,在赵卫东的陪同下,开始彻底清点“金水五金号”的库存。
翻箱倒柜之下,结果令他们既失望又惊喜。
失望的是,材料的质量和数量都极其有限且参差不齐。
惊喜的是,种类之杂、范围之广,远超想象:从最普通的民用五金到一些来路不明、明显是战场捡回来的军品残次件和报废品(锈蚀的枪机、开裂的弹壳、磨秃的撞针、甚至还有几段炸弯的炮管);从各种型号的低碳钢材、黄铜料、铅块到少量的化学原料(结块的硫磺、硝石、甚至还有几瓶标签模糊、存放不当的硝酸和硫酸);还有一些破损的测量工具(卡尺、规尺)、以及几本破烂不堪的英文机械手册和德文武器图册。
“A3低碳钢、H62黄铜…材料基础有一点,但杂质很多,成分不稳定,需要检验和筛选。”
陈景明拿起一块锈迹斑斑的钢料,仔细看了看断口的晶粒,又用手指掂量了一下重量,低声道,“硝酸浓度大概只有40%左右,而且明显变质发黄了,硫酸也有吸湿现象。
量很少,纯度极低,存放条件太差,得想办法重新蒸馏提纯。
这需要非常小心,要有冷凝装置和耐酸器皿,否则极其危险。”
陆维舟则对着一本页角卷起、字迹模糊的英文版《机械原理手册》和一堆奇形怪状的零件发呆,理论上的东西他懂,摩擦系数、应力集中、公差配合、弹道抛物线…但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眼前这些冰冷的、粗糙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实物,他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和挑战欲:“陈工,摩擦系数和材料许用应力我知道怎么算,可这…动手差距太大了。
没有标准的量具,没有稳定的材料性能,甚至没有可靠的动力来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理论是指路明灯,能让我们避免走入死胡同和歧路,能告诉我们最优解的大致方向在哪里。
但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
陈景明拿起一个锈蚀严重的毛瑟步枪枪机部件,仔细检查着磨损和疲劳裂纹,“我们的核心优势,是知道终点在哪里,知道哪些弯路可以彻底避免。
比如,我们知道最优化的弹头应该是什么流线型气动外形,知道膛线缠距如何与弹丸重量、初速匹配才能获得最佳精度和稳定性,知道什么样的发射药燃速曲线最理想…这些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战争检验的、系统性的知识,是这个时代的工匠们靠零散的经验和无数次试错都难以摸索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米’。”
正说着,石大勇那边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和皮带剧烈打滑的噪音,接着是他懊恼又带着点兴奋的嘟囔:“这破皮带!
老化得都没弹性了!
传动轴确实有点弯了!
主轴轴承旷量太大!
齿轮啮合也不严实!
又滑脱了!
这老家伙毛病真不少!
不过…基础架子还行,铸铁床身没裂没变形,导轨磨损不算太离谱,好好调校一番,应该还能用!
比纯手锉强到天上去了!”
陈景云走过去,看着老师傅像对待一位老伙计般,耐心地、一点一点地调试着那台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老机器。
没有电,没有稳定的动力,一切精度和力量都依赖人手摇的感觉和经验。
润滑油散发着变质的气味,皮带上沾满了黑色的橡胶粉末。
这就是一九三零年的中国工业现状,一个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泥潭。
他们未来的每一步,都将是与这种深入骨髓的落后和令人绝望的匮乏进行的艰苦斗争。
傍晚,陈景明独自站在狭窄的后院,看着芜湖城低矮的、鳞次栉比的灰黑色屋檐和远处缓缓沉入江面、如血般猩红的残阳。
屋里,陆维舟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疯狂地在草纸上演算着弹道系数和膛压曲线,试图为他们的“作品”找到理论支撑;石大勇则还在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调试着车床,用油石打磨着刀具,试图让它更听话、更精准一点。
他们三个人,就像三颗偶然落入这片贫瘠、干涸土地的火种。
单颗微不足道,随时可能熄灭。
但若是聚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呵护,相互激发…一个计划的雏形,在陈景明的心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
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安身之所,也不仅仅是一台能工作的车床。
他们需要一座熔炉。
一座不是仅仅用来熔化金属的熔炉,而是一座能熔炼技术、人才和绝望中的希望,最终能锻造出真正守护这个民族血脉与尊严的利器的——熔炉。
而“金水五金号”这间破旧的铺子,就是这熔炉最初、也是最艰难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