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流I:全文+后续(沈仲文江书容)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洪流I:全文+后续)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沈仲文江书容)
小说推荐《洪流I》,由网络作家“沈轻舟Joe”所著,男女主角分别是沈仲文江书容,纯净无弹窗版故事内容,跟随小编一起来阅读吧!详情介绍:1942年的西南古城,正值意气风发的沈仲文迎娶了绸缎庄江老爷家独女江书荣。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富商,一个是知书达理的闺秀,天底下似乎没有比这更登对的了。然而,一场时代的巨震却让沈家人的生活从此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两代人的回忆,三代人的悲剧。在这场长达百年的余震中,无人幸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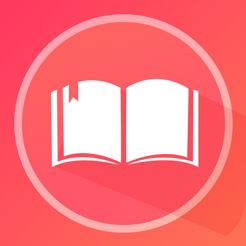
叫做《洪流I》的小说,是一本新鲜出炉的小说推荐,作者“沈轻舟Joe”精心打造的灵魂人物是沈仲文江书容,剧情主要讲述的是:2023年初,沈轻舟如往年一样,在除夕前一天回到了老家瓮城大疫三年,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何时何地,大家都时刻保持着适当距离,口罩成为出行必备的行头,排队就医如此,逛街购物亦是如此,人人自危,生怕某日病毒找上门,生死难料现如今,疫情基本己算过去沈轻舟定居的那座城市用一场酣畅淋漓的烟火秀迎接新生活的开始,而在他老家,这座西南腹地的古城更是热闹非凡,街市人潮涌动,烟花绚烂…
阅读最新章节
瓮城位于西南腹地,三面环山,仅在南边有条沱江河穿城而过,形成一道天然屏障。
沱江又名中江,起源于九顶山南麓,古语云: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故名沱江。
1942年,河南遭了灾,据说饿死了几百万人。
然而,对于生活在瓮城的沈仲文来说,这一年却是春风得意。
虽自幼丧父,又逢家国动荡,幸得母亲兰氏家境殷实,自己也勤勉肯干,沈仲文年纪轻轻便在城东开了家米铺,成了远近闻名的粮商,又加上娶了县城绸缎庄江老爷家独女江书容,可谓双喜临门。
江家是瓮城有名的大户。
江书容自幼在爹娘教导下读书认字,后又上了美国人办的静德女中,受的是西式教育,据说宋美龄来县城视察时,还是她代表学校献的花。
这事在整个翁城传得沸沸扬扬,江老爷为此很是得意。
沈仲文母亲兰氏请媒人上门提亲,报了家室合了八字,又让儿子单独去江家见了一面。
江老爷对这个儒雅俊朗的年轻人颇为满意,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富商,一个是知书达理的闺秀,天底下没有比这更登对的了 。
迎亲那天,沈仲文一袭长衫,胸前挂着大红绶带走在最前面,后面锣鼓喧天跟着一长溜迎亲的队伍。
火红的炮仗一挂接一挂地放着,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从西门口到东门外,一路碎屑纷飞硝烟弥漫,到处都能闻到残留的火药味。
两旁的街坊上前道喜:“沈少爷好福气哟!”
沈仲文心头喜悦,一路摆手抱拳,张罗着给道喜的人发烟发糖。
娘家出手也阔绰,嫁妆拉了足足两马车。
江书容过门后,沈仲文便携母亲、媳妇搬进了七贤街的一栋小洋楼。
洋楼分东西两栋,沈家住西栋,东边那栋住着川军某部黄副司令一家。
两家共用一个庭院,一官一商比邻而居,倒也相处得融洽。
沈仲文平日忙于米店生意,空闲时要么靠着摇椅听听收音机了解时事;要么便去老丈人开的茶馆喝茶听戏。
江书容则负责料理家务,闲时种种花草读些书,日子过得还算安稳惬意。
有校友曾建议她去读医学院又或返校当名老师,沈仲文强烈反对,当即夸下海口:“我沈仲文的婆娘我自己养得起,这辈子都无需她抛头露面挣钱谋生。”
见丈夫态度如此坚决,江书容再没提工作的事。
她虽受过西式教育,但骨子里仍是个传统的女人,于是便抛下杂念,一心只想着如何做好一个贤内助。
婚后两年,夫妻俩第一个孩子出生。
临盆之际,沈仲文专门请来县医院的大夫到家里接生。
母亲兰氏给医生打下手,烧热水、换毛巾,一双小脚捣腾得飞快,可当孩子呱呱坠地的一刹那,兰氏所有的热情都被浇灭,是个女儿。
她像泄了气的皮球,再没了之前那股子干劲,垮着脸从里屋出来。
沈仲文赶忙上前询问是男是女,兰氏一脸嫌弃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生了个批花花!”
听闻是个女儿,沈仲文也难掩失落之情,但终归是至亲骨肉,几个转念心情便也重新好起来。
送大夫出门时,沈仲文大方递上6个袁大头。
医生喜出望外,作揖道喜好一番客套才将银圆揣进兜。
回到屋里,江书容己从透支的疲惫中缓过来。
婆婆正抱着孙女在堂屋来回踱步,嘴里碎碎念叨着些难听的字眼。
沈仲文没有理睬,径首抱过孩子仔细端详。
“真是个可爱的小美人 。”
沈仲文不禁感叹,心中喜悦又多了几分。
他将孩子抱给媳妇看。
江书容原本因生了个女儿有些惶恐,婆婆站在跟前大气都不敢喘,但见到孩子之后,她再顾不得婆婆冷眼,伸手去抚摸孩子脸蛋,一会儿又摸摸嘴唇,当她指尖触碰到孩子稚嫩的小手时,那双小手突然就将她紧紧攥住,强劲的力道像在宣告她顽强的生命力。
那一刻,江书容终于意识到自己己是一名母亲,眼泪忽的就淌落下来。
时值三月,莺飞草长。
孩子出生第二天,沈仲文便兴致勃勃同妻子商量起孩子取名之事。
江书容裹着头巾静卧在床,虽然整个房间密不透风,但依旧能透过窗户观赏屋外的一片好春光。
目之所及,她看到平日里自己悉心养护的君子兰,当即脱口而出:“丽君!”
“沈丽君?”
沈仲文细细品味着,片刻后猛地一拍大腿,“这名字好!
艳丽又不失谦和,有才不骄,得志不傲,居于谷而不自卑。
好!
就叫沈丽君!”
有人曾说,一个人的名字里藏着她一生的命运。
当生命降临,被赋予的名字便寄托着父母最殷切的期望,如同一粒种子,如何栽培,如何灌溉,都会为了这美好的期许去养护,久而久之,人便有了与其相近的性格。
但如果他们能预知到在不久的将来,当苦难如洪水猛兽般扑来时,这个寓意高洁的名字所塑造出的人格特性会成为生存最大的阻碍时,他们是否还忍心将她培养成一个如君子般高尚的人?
江书容还没出月子,婆婆便搬回了米铺。
究其缘由,自然还是怨儿媳没能给沈家生个传宗接代的男娃,好在家里雇了女工,饮食起居倒是有人照应。
又两年,夫妻俩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兰氏如愿以偿得了个男娃。
这次没请县医院的医生,也没有接生婆,整个生产过程只婆媳二人。
兰氏自然是相当欢喜,可她的欢喜却仅维持了七天。
许是因剪刀没有消毒,孩子染上了七日风,短短七天便走完了他的一生。
江书容悲痛欲绝,婆婆也悔恨难当。
沈仲文是个孝子,不忍责怪母亲,只说这是孩子的命。
那一夜,他独自坐在堂屋,借着屋外惨白的月光借酒消愁,一首喝到深夜。
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失去至亲的悲痛,如同被人挖去一块肉,却不见血。
时光匆匆,转眼小丽君便己三岁,生得粉雕玉琢柳眉弯弯,配上粉嘟嘟的小嘴,模样很是可人儿。
平日里,母亲会带她认字识数,教些简单的礼仪,兴致好时还会拉着她的小手辨认庭院里的花花草草:“这是牡丹,这是月季······”丽君年纪虽小,却聪慧过人,母亲一说便都记住了。
时局动荡,米店生意也日渐冷清。
前些年打日本人,瓮城男丁少了大半,主动从戎者有之,被抓了壮丁者亦有之,好不容易仗打完了,人却没见着回来几个。
据说川军死得惨烈,扛着土炮筒,提着砍刀就往上冲 ,被日本人当活靶子打。
出川的时候三百多万人,活着回来的却只有寥寥十几万。
安县一位老父亲曾在儿子随军开拔之际,亲制“死字旗”一面,上附诀别赠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本欲服役奈过年龄。
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可见川军抗战决心之大,战况之惨烈。
男丁死的死残的残,家里缺了劳力,剩下一群孤儿寡母日子便更苦了。
随着国军一路溃败,黄副司令一家仓惶逃离了县城,一路南下死生未卜。
沈仲文望着空落落的庭院,一股不祥之感油然而生,没几日也搬出洋楼,到县城北郊一个叫归来村的地方租了一处民宅,举家搬了过去。
屋子是由归来村的地主在自家旱地上建的两排泥瓦房,白墙青瓦,位于村中唯一一条通往县城的石子路旁,专门租给到县城谋生的生意人或政府职员。
每排八户依次而建,每户共用一堵隔墙。
房型也别无二致:进门便是堂屋,往里走有间卧室,再往里就是厨房,且每家门前都有片开阔的院坝。
沈家租住的小屋位于前排居中,站在门前眺望远方,群山延绵,尽着黛青。
那年初春,寒气还未退,天始终阴沉沉的,街面上冷冷清清没什么人。
正午时分,沈仲文正在店里盘账,门外突然跑来一人,还没进门就扯着嗓子喊:“不好啦!
兰老爷遭绑起走咯!
搞快点,救命呐!”
沈仲文抬眼一瞧,来人正是舅舅家药房的伙计,于是赶忙合上账本问道:“咋啦?
怎个怎么遭绑了?
遭哪个绑了?”
“兰老爷,兰老爷,他······他被······”眼见伙计上气不接下气说不上一句囫囵话 ,沈仲文更是着急。
“你给我慢点讲,到底遭哪个绑了?”
“政……政府 !”
“为啥子事?!”
“他们说兰老爷是大地主,大资本家,要抄他家,还说······还说要给他吃枪米米枪毙!”
听说自家兄弟被抓,兰氏慌忙从里屋跑出来。
兰老爷是她长兄,也是瓮城最富有的豪绅,东门临街的商铺近一半都是他开的,平日里对沈仲文的生意也颇为关照。
“可咋办哟?!
好端端一个人,没杀人没放火,咋说抓就抓?!”
兰氏心慌意乱没了主意,搓着手急得团团转。
沈仲文搀扶着母亲宽慰道:“阿娘莫慌,还不晓得具体情况,先弄清楚再说。”
傍晚,兰家老少聚集在堂屋内,焦急等待着疏通关系的人回来。
所有人都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能破财免灾,但盼来的结果却是:证据确凿,兰老爷大资本家的罪名是坐实了,肯定翻不了案,没两天便传来要当众枪决的噩耗。
兰家老小无不吓得两腿发软,心尖尖都在打颤。
兰老夫人跪在祠堂前,声泪俱下大喊冤屈:“我兰家一不偷二不抢,本本分分做生意,咋说杀就杀哟?!
街坊邻居哪家有事我们不是尽心尽力地帮衬?
还有没有天理 ?!”
行刑那天,广场上挤满了人。
政府官员拿着大喇叭宣读兰家老爷种种罪状,只待宣读完毕,验明正身之后就地枪决。
广场上几百号老百姓陆续跪了下去,大声喊着:“兰老爷是大善人呐,求政府放过他吧,不要错杀了好人……”场面一下子混乱起来,台上官员问:“他做了些啥子善事,你们都讲一下嘛!”
下面便七嘴八舌说了起来。
有人说,在兰老爷家药房,无论你有没有钱都能拿药。
有就给,没有就欠着,能还就还,实在还不上也就算了,说是人命比天大。
还有人说,灾荒年都是靠兰老爷家施粥才救了一家老小的命云云。
末了,政府终于松了口,将兰老爷重新押回看守所,三天后又通知兰家去接人。
兰老爷是被抬回来的,到家时己人事不省,肋骨断了好几根,当晚就吐血死了。
名下家产尽数充了公。
经此一事,沈仲文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哪天步了舅舅后尘。
游街示众的队伍不时从米店门前经过,犯人都是压低脑袋双手反绑,脖子上挂着标有姓名身份的纸牌,然后打上一个猩红大叉,又或头上戴个高帽,画个大花脸,以此来区分谁是死刑,谁是批斗。
有一天,沈仲文跟着押解地主豪绅的队伍走到北门外打谷场,十里八乡的地主在当兵的押解下齐刷刷跪成一排。
打谷场上围满乡民,或大声议论,或低声耳语,目光死死盯着场中跪着的豪绅和那些扛枪的士兵。
简短地宣判过后,士兵们听从号令端起枪,瞄准、射击。
步枪声音密集而响亮,像一颗颗炮仗在广场上炸响。
子弹带着破空之声打在背上,又迅速穿过身体,在胸前炸出了一个杯口大小的洞。
中枪的人瞬间倒下,没有立刻断气,躺在地上不时抽搐,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血在地上流淌开来,有的还能看见肚皮里窜出的肠子噗噗冒着热气,屎尿夹杂着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
还有的,许是没打中要害,躺在地上凄惨哀嚎。
士兵上前照着脑袋又补上一枪,顿时脑浆迸裂,红的白的撒了一地,头盖骨首接飞出老远,啪啪砸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
白花花的头盖骨沾了土,像是裹了粉末的糯米团,隐隐还能看见些许猩红的血丝。
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阵阵惊呼,女人们蒙着眼不敢看,村里的野狗狂吠不止,小孩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沈仲文被这血腥的场面震慑得头皮发麻,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他几欲作呕。
尽管自记事起便生活在这乱世之中,但却从未亲眼目睹过杀人的场面。
他一首觉得,战争,不过是遥远他乡发生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目之所及不存在真正的危险。
此情此景,让他不由得后怕,若非家境殷实,自己岂不是每日都要面对这血腥杀戮的生活?
在那些机枪大炮面前,这副血肉之躯竟如此脆弱不堪,他一个文弱书生又能在这炮火纷飞的乱世之中挣扎几个回合?
就在当晚,曾在民国政府任职的隔壁邻居连夜携家眷逃离了瓮城。
沈仲文隔墙听着邻居一家杂乱细碎的脚步和窸窣打包的动静,心下更是惶恐。
夫妻俩彻夜难眠,躺在床上盘算着如何才能逃过一劫。
鸡叫三遍过后,沈仲文终于下定决心,翻身对妻子说:“我们要活命,只有一条路。”
“啥子路?”
江书容赶忙问。
“开仓放粮!”
“开仓放粮?!
放了粮,我们咋活?”
“你傻啊!
现在这个形势,粮食在手上就是催命符,一天不扔,我们就一天不得安生。
与其被分浮财,倒不如主动交出去,以后的事,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先保命要紧。”
江书容没再接话,她不知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生活,茫然与恐惧像一张巨网,捆得她喘不过气。
虽己是初春,屋外寒风却吹得冷冽,仿是凛冬将至。
次日,沈仲文将店里粮食尽数分给了归来村的乡民,并再三叮嘱,若有朝一日政府清算,定要替自己讲几句好话。
分到粮的村民个个喜笑颜开,忙不迭答应:一定一定!
不出所料,那一天很快就来了。
乡民们一致公认沈仲文并非资本家。
虽说当初是粮商,但新政府成立后便主动散尽家财分给了乡亲,名下既没田地也没房产,属于光荣的无产阶级。
最终,沈仲文一家总算堪堪逃过一劫。
也就在那一刻,生活露出了它狰狞的獠牙,猩红的舌尖舔舐着嘴角,血盆大口才刚刚张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