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自己对话休谟休谟完本小说阅读_免费小说全本阅读与我自己对话休谟休谟
《与我自己对话》是由作者“好v火锅”创作的火热小说。讲述了:自言自语,我经常发呆,所以我要把我的胡言乱语记录下来,我喜欢自己说话,位我上者灿烂星空,位我心中道德律令…
小说叫做《与我自己对话》是“好v火锅”的小说。内容精选:休谟觉得呀,如果一个哲学概念或者原理,在现实中找不到相对应的知觉或者印象,那它就是虚构出来的你看,这就说明了,判断哲学概念和原理的标准是感觉和印象,而不是什么客观事实或者实践哦在休谟的眼里,感觉的来源是个大难题,感觉没办法超越自己去体验知觉和对象之间的联系所以呢,他就干脆不考虑感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东西的问题啦他不仅把物质实体给否定了,连精神实体也一起否定了呢这么一来,除了人的感觉,其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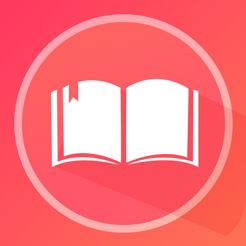
热门章节免费阅读
休谟觉得呀,如果一个哲学概念或者原理,在现实中找不到相对应的知觉或者印象,那它就是虚构出来的。
你看,这就说明了,判断哲学概念和原理的标准是感觉和印象,而不是什么客观事实或者实践哦。
在休谟的眼里,感觉的来源是个大难题,感觉没办法超越自己去体验知觉和对象之间的联系。
所以呢,他就干脆不考虑感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东西的问题啦。
他不仅把物质实体给否定了,连精神实体也一起否定了呢。
这么一来,除了人的感觉,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存在,就都不知道喽。
休谟还认为,因果性只是“习惯的联想”。
自然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客观的必然的因果联系。
因果联系的观念,来源于人们的“习惯联想”。
由于原因与结果很接近;原因在前,结果在后;二者经常连结在一起;所以,当一事物出现时,人们就自然联想到另一事物的出现。
这种“联想”就是因果关系的本质。
“必然联系”观念只是心灵的习惯,并非客观实在。
由于休谟认为凡不首接呈现于感觉印象的东西,我们便对它不能有任何观念,所以他认为我们只能感知孤立的事情,而不能感觉到它们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个错误结论正是休谟否定理性认识造成的恶果。
休谟指出,人类理性研究的对象宛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分为两类:一类是观念的关系,宛如永恒不变的北极星,在夜空中闪耀着永远可靠的光芒;而另一类则是事实,恰似夜空中瞬息万变的流星,稍纵即逝,没有客观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他认为第一类即数学知识,它们与事实的经验无关,是永远可靠的自明的。
而关于事实的知识即经验科学,就只能是“或然的”,没有客观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休谟在宗教问题上的思想如同一团迷雾,令人困惑不己。
他一方面将怀疑论进行到底,否定精神实体的存在,让上帝的存在变得扑朔迷离,同时对有神论的论据如“宇宙论证明神迹宇宙设计说”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认为宗教的基础不过是迷信和狂热。
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坚信上帝的存在,认为普通人需要宗教信仰,有教养的人更需要“真正的宗教”,因为宗教“是道德的可靠根基,社会最坚固的支柱”。
他认为,成为哲学上的怀疑论者,是成为健全而虔诚的基督徒的第一步。
休谟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与动摇,正是当时资产阶级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犹豫不决的真实写照。
休谟的不可知论,对后来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康德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人们在理证科学中所建立的一切规则都是确定无误的。
但是,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受到那些容易发生错误的、不准确的感官的影响,我们往往背离这些规则而陷入谬误之中。
因此,我们所作的每一段推理都应有一个新的判断依据,借此来检验或审视我们最初的判断或信念;而且,我们必须将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将之用以审视认知欺骗过我们的例子之上,并将这些例子与具备正确且真实的认知依据的例子进行比较。
我们必须把理性视作一个原因,而真理则是这一原因的自然的结果。
但是,理性由于受到其他原因的影响,以及我们自身心理上的动摇,而往往受到阻碍。
这样,所有的知识就蜕变为可能性推断。
而这种可能性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它取决于我们所体验到的认知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问题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没有哪位认真钻研态度严肃的代数学家或数学家会全然接受他刚刚发现的某个假设,将之信为完全的真理,而不是将之视为一个单纯的可能性推断。
他对该假设的信心随着其对该假设的检查与证明的增加而增加,更因为其朋友的赞许而增加。
而如果学术界一致接受这一理论,并表现出赞许之情的话,那他的这种信念也就达到巅峰。
很显然,这种信念的增加只是可能性不断累积的结果,而且发生于我们对过去的经验和因果之间恒常结合的观察。
对于那些较长或是较为重要的账目,商人总是不大相信他们所记载的数目是完全无误的,而是选择采取人为计算的方式,用一种会计师的技术与经验所不能得到的可能性推断的方式来进行推算。
很显然,计算本身是某种程度的可能性推断,这种可能性推断随着那人的经验多少与账目长短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既然没有人会认为我们对一连串计算的信任会超出可能性判断以外,那么,我们便可以断定:几乎没有哪个与数字相关的命题,可以使得我们对其产生比可能性推断更为充分的确定与保证。
因为,我们在将数字逐渐减少之后,我们不难将那些最长的加法演练归纳为最为简单的问题,成为两个单纯的数字相加;根据这个假设,我们很难找出划分知识与可能性推断之间的界限,或者发现知识的终结点与可能性推断开端点的那一数目。
无论如何,知识与可能性推断二者是完全相反的、即截然相反的,它们无法发生潜移默化的相互渗透。
因为,它们都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要么完全存在,要么完全不存在。
此外,如果一个加算是正确的,那组成这个加算的每一次算法应该也是正确的,所以整个数目必然也是正确的,除非我们认为整体与其他部分不相同。
我之前己经说过,这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通过反思,我又感觉到,这与其他推理一样,必然会有一种不断弱化的过程,结果从知识减为可能性推断。
所有的知识既然都归为可能性推断,最终成为属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信据一样的存在,那我们现在就应研究后面这一种推理,看它建立于何种基础之上。
在形成有关可能性推理的每个判断中,就与我们有关知识的各个判断中,我们应将从认知本性处所获得的另一个推断,来改正我们从该对象的本性处所获得的最初判断。
我们知道并可以确定,一个拥有见识与经验的人,比起一个愚昧无知的人而言,前者对其观点应该有而且通常也确实有较大的信心;而我们的观点随着理性与经验程度,甚至对自己而言,也存在着不同的信据程度。
对于那些拥有最高见识与最为丰富经验的人而言,这种信据必然也不是完整的。
因为,即便是那样一个人,他必然还是可以感受到过去的种种错误,因此担心未来也会发生同样的错误。
所以,此处就产生了由一个新的可能性推断来调整与改正最初的可能性推断,从而确定其相应的标准与比例。
如同论证要经受可能性推断的检验一样,可能性推断也借助于心灵的反思而得到改正;这种反思作用所指向的对象便是人类的认知本质和根据最初的可能性推断而进行的推理。
既然我们在每个可能性推断中,除了那一研究对象那种原始的不确定性本质之外,发现了因为判断这一感官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我们己将之调整起来,那现在我们就为理性所胁迫,以一种新的怀疑加于其上;这种怀疑产生于我们在判断感官的真实与否、可靠与否时所犯下的错误。
这时很快就出现与我们之前的一种怀疑,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解答。
不过,这种解答必然有助于我们之前的推断,但是,因为它建立于可能性之上,那它必然更会弱化我们的原始信据。
而其本身,必然会因为同样性质的第西种怀疑的影响而弱化,如此无限循环往复,首到最后,最初的可能性一点也不存在为止,而不管我们如何假设它之前是如何之大,也不管每一次新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减弱是如何之小。
不管是什么有限的对象,它在经过无数次的一减再减之后,都无法继续再存在;即便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大数量,按照这个方式最终也必然会归于消灭。
不管我们之初的信心是如何之强,在经过那么多次新的研究之下,在每一次的研究中其潜力与活性不断受到弱化。
所以,到最后,这种信据必然会消失殆尽。
我对我的判断所可能会产生的错误进行反思,与我单单研究对其进行推理的那一对象相比,前者使得我的观点的信心更为缩减;而如果我再进一步,仔细研究我对感官所作的那些评论时,所有的逻辑规则都不断地将我的信心减弱,乃至最后我的信心与信据都消失殆尽。
如果有人说,我是否真的同意我现在不厌其烦地进行的这一论证,我是否属于那些怀疑主义者之一,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认为我们对任何事情上的判断都不存在任何鉴别真伪的标准?
那我对此要回答说:这种问题是完全多余的,不论是我还是他人,都不会真诚地坚持这一观点。
自然借助于一种绝对的、不可控制的必然性决定着我们要呼吸会有感觉,不仅如此,它还同样决定着我们要进行判断。
考虑到那些对象与当前的感知存在着一种习惯性的关联,所以我们便不得不以一种强烈的、充分的方式来看待那些对象。
这就好比我们在醒了的时候无法不思考,好比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总是可以看到左右的物体而无法阻止自己不看到一样。
如果有人费心试图对这个完全怀疑主义进行吹毛求疵的反驳,那我敢确信,他必然找不到辩论的另一方。
而且,这种辩论必然是在通过己经在心灵中树立起的并使之活动的感官而进行的。
之所以我能如此细致地阐述那一狂妄学派的种种论证,乃是因为我试图使读者感觉到我的假设的真实性,此处我们的假设是:有关因果的一切推理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且,确切地讲,信据是我们天性中感性部分的活动,而非我们认识部分的活动。
此处,我己经证明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原则来对所有的话题进行判断,而且通过研究我们在思考该话题时所运用的天才、能力与心态来校正这种推断。
的确,我己经证明了,这些原则在向前推进而运用于所有新的反思判断时,会由于不断弱化而使得其信据不断减少,最终消灭殆尽,因此,所有的信心与观点就会归于无有。
所以,如果信心真的是一种单纯的思想活动,而没有任何特殊的想象方式,或者说不存在那么一种力量与活性,那么它必然会将自身毁灭掉;而且在所有情形下,它最后都会使得判断陷入僵局之中。
但是,既然经验可以使得那些乐于尝试的人相信,他在之前的推理论证中决然不会发现任何错误的存在。
尽管如此,他还是会继续地相信着、思考着、推理着。
既然如此,他便可以说,他的推理与信心是一种感觉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想象方式,单纯的认知与反思是无法将之消灭的。
不过,或许有人会在此处问,根据我的假设,上面所说的那些论证为什么不会使我们的判断陷入完全的停顿呢?
心灵又是依靠何种方式来对某个话题保留一定的信心呢?
由于不断地重复,那些新的可能性推断其信据不断弱化,它与原始的判断所赖的准则是相同的,当然,这并非是说与那些思想或感觉的准则相当。
接下来,我们便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不论是何种情形,它们必然都会将原始的判断推翻掉;而且,由于各种相对立的思想或感觉,它们必然会使得心灵陷入完全不确定之中。
假设人们向我提问,而我在考虑我的记忆感知与感官感知,并将思想由这些感知转移到与之通常结合的那些对象之上后;我就感觉到某一面与另一面相比,有着更为强烈的、更为有力的想象。
正是这种强烈的想象,构成了我的第一个断言。
假设后来由于我研究判断力本身,我通过经验发现,这一判断有时是正确的,有时候是错误的;于是,我就认为我的判断力是由若干个相对立的准则或原因所综合影响;而这些准则之中,有些带来真理,有些带来错误;在将这些相反原因彼此抵消掉之后,我就通过一个新的可能性推断使得我弱化了第一个判断的信心。
与前面那一可能性推断一样,这一新的可能性推断也会同样地受到削弱,如此循环再循环。
所以,有人或许就会问,为什么我们还能保留那些我们在哲学上或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那种信心程度呢?
我的回答是:在经过第一次与第二次的推断之后,心灵的活动便较为消极且不自然,我们的认知开始变得微弱、模糊,判断力的准则以及各个相对立的准则相互抵消。
虽然还是如之前一般发挥作用,但是,它们在我们的想象上的影响,与他们加于思想上或从思想上减去的力量,其实与之前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的心灵无法方便顺利地达到其对象,那同样的准则就不像我们在自然设定各个认知时所产生的印象。
想象在那种情况下所感受到的感觉,也与平常的判断与观点所产生的那种感觉不成比例。
此时我们的注意就紧张起来了,心情变得摇摆不定,精神因为偏离了自然的途径,所支配着精神的那些法则就与支配着我们的精神的平常运行方式的那些法则也就不同。
至少,那些法则的作用力达不到平常所能达到的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要找出相似的例子,那倒也不难。
现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一形而上学的话题,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素材。
有关历史和政治学上的一些推理中,本来可以视作很具说服力的那种论证,对于这些深奥的话题几乎不具备任何影响,即便人们完全理解那种论证。
这是因为,哲学上的推理论证,需要的是思想上的勤奋与研究,只有这样,这些论证才能为人所理解。
而这种思想的努力,将我们信心所依赖的那种情绪作用打乱。
其他主题上,也是如此情形。
想象如果变得紧张起来,就必然会影响到情感和情绪的正常进行。
如果一个悲剧的作者将其主角描写为虽然身处种种困难与忧伤之中,仍然保持警觉及其幽默,仍然能侃侃而谈,风趣非凡,这样是绝对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的。
心灵的情绪不仅会阻碍我们做出精细的推理与反思,同样地,后面那些心灵活动也对前者有害。
心灵,就如身体一样,似乎具备着某种确实的力量与活动;在将这种力量付诸活动中时,不得不暂时停止其他活动。
这一情形在各个不同性质的活动中,尤为真实具体。
因为,在那种情形下,我们的心灵的力量偏于一个方面,而且心情甚至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这使得我们无法由一个活动转移到另一个之上,更不可能同时进行两个活动。
所以,想象总是试着进入一个推理过程,而且在想象各个部分时,因这种精细的推理而产生的信心就随着这一努力的比较而得到弱化。
信念,是一种较为生动的想象,如果它不是建立于一种自然、顺利的对象之上,那它永远不会是完整的。
在我看来,这便是问题的真相所在。
我不同意有些人对怀疑主义者采取的那种首接的方法;他们没有任何研究或思考就首接将后者的论证都予以否定。
这些人认为,如果怀疑主义的推理是有力的,那就是说理性还存在着力量或权威;而如果这些推理是站不住脚的,那它们永远无法使得我们有关认知的结论变得无效。
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怀疑主义的推理可以存在,如果怀疑主义的推理无法为其佶屈聱牙所毁灭,那么它们必然会随着我们的心情所发生的变化而变化,时强时弱。
而理性从最开始便占据着优势,以绝对的权威与力量制定规则、确定原理。
所以,理性的敌人被迫隐藏起来,在其阴影之下,借助于合乎理性的论证来阐述它的错误与愚蠢;所以,这可以说是在李性的签字盖章下获得了特许。
这一特许从一开始,就以理性的当前的首接权威为依据,这是其产生的依据,也就成了作用力的依据所在。
但是,既然我们假设该特许是与理性相矛盾,所以它就逐渐地减弱了那一统治权的力量,也减弱了其自身的力量;首到最后,二者都因为不断的递减而完全消失。
怀疑的理性与专断的理性同属一类,虽然它们的作用与趋势不同。
所以,在专断的理性强大时,它就需要对付怀疑的理性,将之视为其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一开始,二者的力量是均等的,所以只要有一方还存在着,它们便可以继续共存。
在二者的这种斗争中,一方所失去的力量便是另一方所获得的力量。
所以,自然可以及时将一切怀疑主义论证的力量消灭,使其无法对人的认知产生较大影响,这可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我们如果想任由其子
小说《与我自己对话》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
